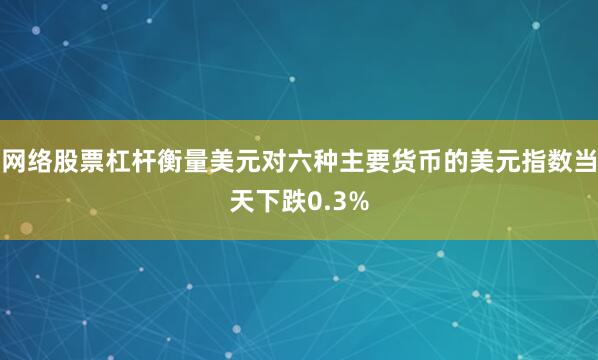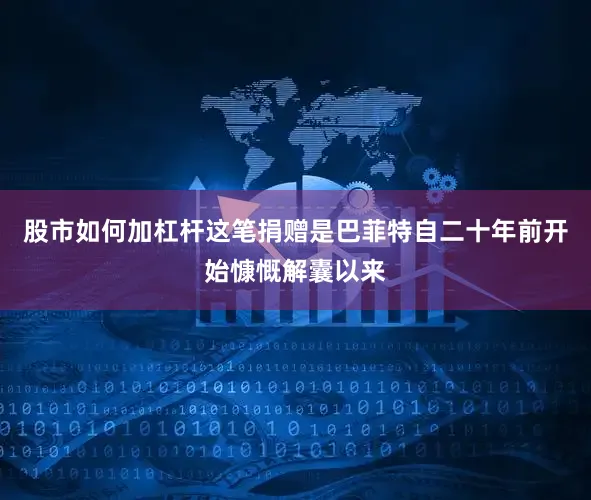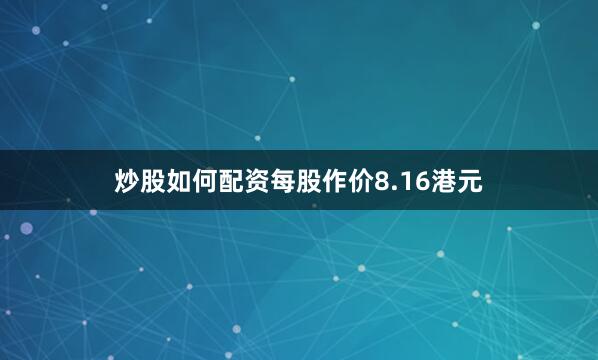文/潘彩霞(改写版)
1979年,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后,著名翻译家巫宁坤终于再次见到了她的师姐赵萝蕤。巫宁坤心中感慨万千:“此身虽在,堪惊。”
眼前的赵萝蕤因精神分裂症的困扰,嘴唇时常不由自主地抽搐,令人心疼。回想起当年那个温文尔雅、气质非凡的大家姐,巫宁坤心头一阵酸楚。得知她仍需依赖药物维持精神状态,他关切地问:“药量能否适当减少一些?”
然而,赵萝蕤神色骤变,声音里带着质问:“你难道想让我病情加重吗?”
她的丈夫陈梦家自杀已经十多年,那段人生最痛苦的时光,她只藏于心底,从未向人提及,只把所有思念埋藏在两人共同深爱的诗文之中。
展开剩余87%赵萝蕤出身于一个大学教授家庭,自幼读书早,是名副其实的“温室花朵”。在遇见陈梦家之前,她一直被宠爱和骄傲包围。
她的父亲赵紫宸是燕京大学教授,聪颖的她从小学习优异,多次跳级,16岁便考入燕京大学。
两年后,她从中文系转向了西方文学专业。那时的她,常在燕大朗润园的草坪上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《皆大欢喜》,她的才情与风采让无数青年为之倾倒。
钢琴弹得优美,文章写得出色,举止文雅端庄,赵萝蕤很快赢得了“校花”的美誉,追求者络绎不绝。可她性格内向拘谨,严肃得如同山岳一般,除了专心读书,几乎不与人亲近。
20岁那年,赵萝蕤从燕京大学毕业,以英语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。她容貌出众,才华横溢,身边追求者不少,但她的心中唯独钟情那个与她保持距离的男子——陈梦家。
当时,陈梦家在燕京大学专研古文字学,是浙江人,少年成名。在中央大学读书时,他便与闻一多、徐志摩齐名,成为“新月派”诗人的代表人物。史学大家钱穆曾评价他“长衫飘逸,颇具中国文学家的风范”。
尽管才华横溢且仪表堂堂,陈梦家出身寒门,对家世显赫的赵萝蕤始终保持敬重,从未冒犯。更何况,他刚刚经历与孙多慈的感情失败。
赵萝蕤并不顾及门第观念,她眼中,陈梦家才华绝伦,风采无双。她主动追求他,尽管她的诗风与“新月派”南辕北辙,但只要陈梦家参加的文艺活动,她必定出席。
有人问她:“你喜欢他的诗吗?”她坦率地说:“不,我是喜欢他长得漂亮!”
他们这对才子佳人,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1933年,两人合作翻译了《白雷客诗选》,在报纸发表时,署名是“萝蕤·梦家”。
那段时间,赵萝蕤的诗作渐多,她将几首寄给戴望舒,很快被刊出。戴望舒还邀请她翻译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《荒原》。
《荒原》以其晦涩难懂和引用渊博著称,赵萝蕤不负众望,展现了惊人的翻译才华,年仅23岁。
两年后,她的《荒原》译本问世,一举成名。诗人邢光祖赞誉道:“艾略特的这部长诗如同现代诗歌的‘荒原’中的灵芝,而赵女士的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奇葩。”
然而,爱情遭遇了现实的阻碍——陈梦家家境贫寒,赵萝蕤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恋情。
赵萝蕤没有退缩,面对家里的经济断供,她一度向好友杨绛借钱度日。
最终,她的真诚与坚持赢得了家人的认可,1936年,两人在燕京大学举办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,才子佳人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。
1937年,抗战全面爆发,陈梦家远赴西南联大任教。根据清华旧规,夫妻不能同时在一校任教,为了支持丈夫,赵萝蕤选择回归家庭。
她坦言:“我是老思想,妻子理应为丈夫牺牲。”曾经的大小姐从此洗衣做饭,淘米烧菜,甚至学会了种菜养花。
然而,她依然是热爱读书的学者,家务之余,依然手不释卷,几乎读遍了联大图书馆的英文文学藏书。
柴米油盐的生活中,她常在做饭时膝头放着一本狄更斯的书,享受着明月清风的精神世界。
1944年,陈梦家受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,夫妻二人携手前往深造。在她犹豫是攻读硕士还是博士时,陈梦家鼓励她:“你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!”
在这所世界顶尖学府,赵萝蕤如鱼得水,学业之余,夫妻二人一同欣赏音乐、观看戏剧、参观博物馆,拜访古董商,从书本到艺术,他们共享彼此的热爱,感情愈发深厚。
陈梦家才华横溢,编写了中国铜器图录,并用英文发表多篇论文,这为他后来的收藏与考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更令人欣喜的是,他们受到了艾略特的邀请,参加晚宴时,赵萝蕤带去的诗集上,艾略特欣然签名题词:“献给赵萝蕤,感谢她对《荒原》的翻译。”
1947年,陈梦家先回国,在清华任教,而赵萝蕤留在美国继续完成博士论文。隔着重洋,夫妻间的关爱依旧通过书信传递。
得知她想做衣服,他写信说:“小妹,听你要做衣服,到那家店里挑一件古铜色的缎子做里子。”
买了些小古董,他汇报:“这东西别人不一定懂,可将来若遇困境,能卖个好价钱。你看了会高兴的,等我拍照发给你。”
能与她分享生活中的点滴,他的小幸福跃然文字间。
1948年底,国内战事紧张,赵萝蕤担忧不能与陈梦家团聚,毅然放弃即将取得的博士学位,登船回国。
历经坎坷,她平安抵达北平。城门打开的那一刻,她看到前来迎接的陈梦家,阳光下他依旧风华绝代,宛如当年少年。
回国后,赵萝蕤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。她与陈梦家住在朗润园的一幢中式平房里,花木扶疏,荷香扑鼻,室内陈设明代家具古朴典雅,摆放着一架“斯坦威”钢琴,中西文化相得益彰。
不久,朝鲜战争爆发,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返国,赵萝蕤被任命为西语系主任。她信心满满,描绘着建设优秀英语专业的蓝图,并邀请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的巫宁坤回国任教。
1951年8月,巫宁坤抵达北京,赵萝蕤亲自到火车站迎接。巫宁坤敏锐地察觉到,昔日那个穿着素色西装、气质大方的师姐,此刻身穿褪色的灰布中山服,衣衫皱巴巴,神情憔悴,形象迥异。
没过多久,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而来,赵萝蕤忙于参加各类会议,进行自我检讨,身心疲惫。燕京大学被撤销后,她的理想破碎,宣布调入北大那天,她失声痛哭。
幸有陈梦家慰藉。他调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,夫妻两人虽然分居,但在信中他不断安慰:“你放心。”
完成《殷虚卜辞综述》后,他用稿费买了一座四合院,为赵萝蕤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,帮助她疗愈身心的创伤。
多年后,赵萝蕤回忆那段平静时光:“有时半夜醒来,还看见梦家屋子里的灯亮着,他或写作,或欣赏家具,静静地坐在那里,似乎在用心与这些老物件交流。”
1957年,不幸降临。因提出批评意见,陈梦家被打成右派,遭受不公待遇。赵萝蕤也因打击精神失常,被送往医院治疗。两人抱头痛哭,心痛难忍。
后来,陈梦家被下放劳动,心系妻子,几乎每天写信鼓励她,字里行间温暖而朴实:“你的健康是我最大的牵挂,其实你已经好多了。”
“我理发时没剃胡子,棉衣脏了,你见了不要怕。”
他最想说的,是那句:“我们必须活下去,但得把心放宽些。”
然而,最后没能挺过来的,是他。1966年,陈梦家忍受不了屈辱,在自家小院的一棵树上结束了生命。
十年后,赵萝蕤从劫难中重生,尽管多年病痛缠身,药物维持下嘴唇依然抽搐。健康稍有好转后,她回到北京大学任教。
此后,她拒绝提及陈梦家,课余时间,她伏案于父母旧居的小书桌旁,凭借衰弱的身体和昏花的双眼,开始翻译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巨作《草叶集》,持续了整整十二年。
1991年,《草叶集》全译本出版,在学术界引起轰动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头版刊发长篇报道,称赞:“一位中国学者如此执着且雄心勃勃地翻译这位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,令人惊叹。”
那年,赵萝蕤已79岁。正值母校芝加哥大学百年校庆,她应邀出席相关活动。
在芝加哥美术馆,她见到了陈梦家编著的《中国铜器图录》展出,顿时泪如雨下。
回望往昔,留美的岁月历历在目。她从未忘记他的叮嘱:“你不能放弃文学事业。”
时光虽短,艺术永恒。赵萝蕤虽未在诗中书写爱情,却因爱而在荒原中微笑绽放,创造了奇迹。
他始终活在她生命中,从未离去,亦无人能替代。萝蕤·梦家的名字,永远紧紧相连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华夏配资网-股票杠杆的平台-股票配资网大全-炒股如何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